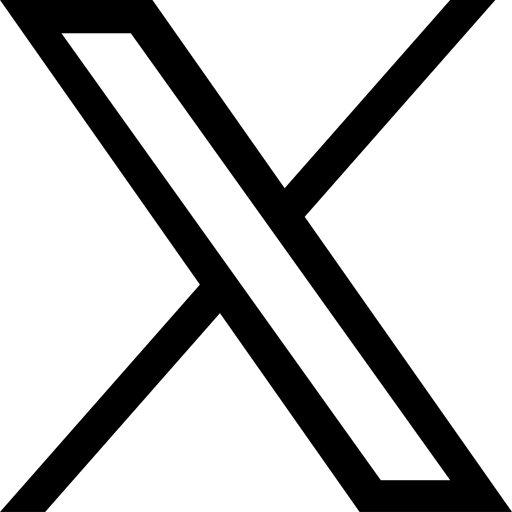14/11/2018
我的金庸年代
中文從來不是一樣容易學習的科目。小時候最怕執筆寫字,一來筆劃艱深,二來詞語缺乏,所以作文三百字,要用只有一節半小時的課,去創作往往要花經年去完成的文章,我寧可逃學,躲在洗手間廁格。躲在廁格無事可做,唯有偷帶金庸小說陪伴。
金庸小說曾出版過袖珍,碧血劍是我的第一本閱讀的金庸著作。曠課前把一本小袖珍藏用褲頭皮帶夾住,像韋小寶一樣在皇宮中越過各太監待衛,竄到教室外的洗手間,只把馬桶蓋翻下,取出小說,比時下的穿越劇更早懂得穿越時空的樂趣。
四小册的碧血劍,對小學的我來說,是一本好比二十四史般長的作品,但何時何地均手不釋卷,無論是課間空隙,抑或課餘時間,都讀很滋味。這種沉迷,相信只要曾揭過一頁金庸小說的讀者,皆有嘗過。
好在當時離文革已遠,查良鏞不再被開宗明義標籤成叛徒,加上我讀的是天主教小學,中文老師即使早知我永無出息,至少也多勸我開卷,他也似乎默許我讀金庸著作。
金庸小說比中文教科書好看多了。不是貶抑其他在中文教科書內的作家,而是教科書內往往只是節錄,或一兩篇散文隨筆,然而一齣精彩電影,切頭裁末,像驗尿一樣,只看局部的幾句對白,這能有多理解和細味電影中的優秀處?
在學校學習中文,像偷看江湖各門派的招式:在岳不群裏學一劍,於洪七公身上學幾招,然後互相併攏,成為自己所學。中文教科書的編排,偏偏像平一指與胡青牛學武功,讓你的武術上永遠不可能成為大家。學習中文,要選一本有地位的著作視為秘笈,慢慢嘴嚼。看白先勇的,就學白先勇的「繞指柔劍」;看張愛玲的,就學張愛玲的「綿掌」;看古龍的,就學古龍的「一字電劍」。否則一句寫來,各沾幾筆,挽幾個劍花,原來一概不通。
雖然旁邊的廁格偶爾傳來隱隱攻鼻氣味,但又何妨?心思早就伴隨書中文字,飄到九霄之外。我蹲在馬桶上,洋洋地過了一個下午。
《經濟通》所刊的署名及/或不署名文章,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,並不代表《經濟通》立場,《經濟通》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。
【你點睇?】當局料聖誕新年期間逾1300萬人次出入境,較去年同期大增。你對本港聖誕新年市道是否有信心?會否出境旅遊?► 立即投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