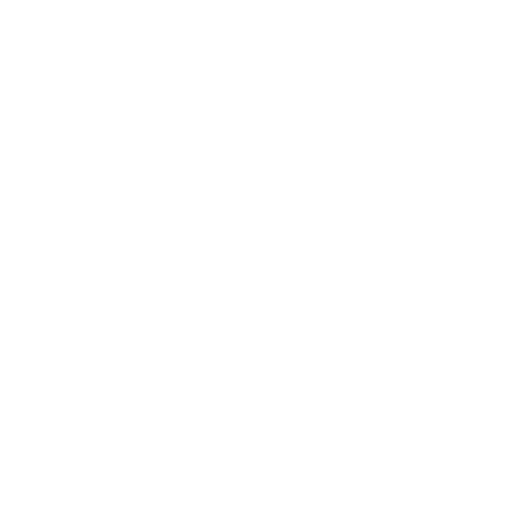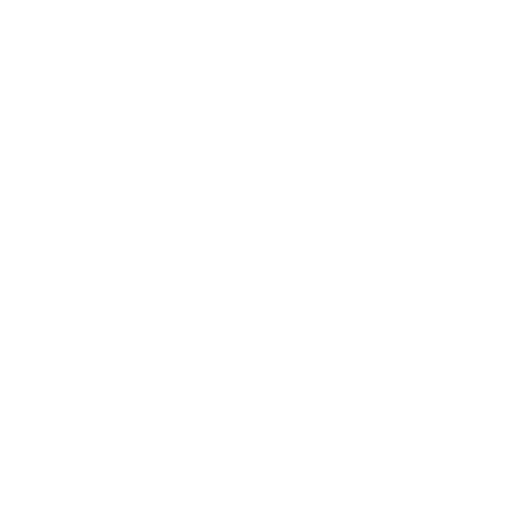24/06/2014
天目情
宋、元時期的黑釉瓷器一直以來都是日本人的至愛,尤其是與日本茶道有關的黑釉碗和黑釉瓶子,更是每一個日本收藏家和茶道愛好者夢寐以求的珍品。
日本人稱黑釉瓷器為天目(Tenmoku),當中國大陸還是一窮二白的時候,大量建窰器、磁州窰器和吉州窰器以賤價賣去日本。我記得在九十年代初,大量黑釉瓷器出現在上環永吉街誠利商場的古董店,一隻完整的宋代建窰兔毫盞只售幾百元至幾千元不等。店家通常將一百幾十隻建窰兔毫盞分幾排疊在一起放在地上,當它們是爛缸瓦。我去買貨時常常蹲在地上一蹲就是一個半個鐘,逐件看,如驗屍一般,又怕假,又怕有衝,又怕有修補,真是為兩餐令到自己儀態盡失。
當年在寸嘴的店家那裏買建窰兔毫盞非常受氣,一掏出放大鏡,店家就衝著你問:
「買嗰幾千蚊嘢,使唔使用放大鏡咁大陣仗?」
不用放大鏡,唯有學盲俠勝新太郎一樣聽聲,用一個壹元硬幣這裏輕輕敲敲,那裏輕輕敲敲,聽聽有沒有修補,聲音是否清脆,有沒有啞聲。

南宋建窰「禾目天目」盞
某一天,一位日本美女走進我的小店,在飾櫃前看了十多分鐘後,問我飾櫃裏的黑釉碗是不是建窰兔毫盞、是真是假。生客問我的貨是真是假,我通常不答,美女當然另作別論。我拿出建窰兔毫盞放在書枱上,招呼她坐下後,用了差不多十五分鐘詳細解釋建窰兔毫盞的特徴、如何分辨真假。她看上去好像聽到津津有味,還不斷問問題,還告訴我灰色兔毫的建窰碗在日本稱「禾目天目」,還教我用日文唸「禾目天目」。
賣一隻一萬多的碗用了差不多一個小時,日本美女走後我的夥計稱讚我非常專業,說未見過我對一個生客如此有耐性。她的話裏有話,我當然聽得懂。
幾個月後,日本美女寄給我一張明信片,告訴我東京某私人博物館將會舉辦一個天目碗展覽,展出的天目碗全是國寶級精品,邀請我到東京跟她一起參觀。
日本所藏的國寶級天目碗我知之甚詳,但一直無緣親炙,今有美女邀請一起參觀,恨不得借滕王閣的順風,一陣吹我到東京。

南宋建窰兔毫盞
到達東京成田機場已是晚上八時多,乘Skyliner到達上野時已是深夜。八十年初我曾被受聘的銀行派駐東京,住在大手町住了差不多半年,之後每年總有一、兩次到東京出差,對東京不可謂不熟。轉車到銀座日本美女替我訂的酒店只是少於半小時的車程,一推門進入酒店大堂已見她坐在梳化上等候。我們一見如故,她笑口盈盈說要帶我見識六本木的夜生活,叫我快些放下行李,跟她一起走。
六本木我在八十年代到過不下數十次,大部份時候都是跟一個英籍同事Charlie一起。他熱衷識日本女仔、玩一夜情,我親眼目睹他從六本木帶回酒店的日本女仔不會少於二十個。他非常博愛,博愛到只要順手,不理好醜。他不英俊,也不是高大威猛,但就笑口常開、口甜舌滑,說話常常如天花亂墜,一陣子就勾搭上一個他眼中的美女,讓她挽著臂彎,跟他回大手町的酒店。
我們在六本木一間比較清靜的酒吧坐下不久,她的話匣子一打開便滔滔不絕,跟在半年前她第一次跟我說話時的拘謹態度簡直判若兩人。她說很喜歡我賣給她的「禾目天目」,說愈看愈喜愛,又說能跟我一起參觀、聽我講解日本私人博物館所藏的國寶級天目碗非常開心,多謝我遠道而來。Charlie鍾情於「即食麵」,我卻陶醉於喁喁私語之中。
第二天一早我在酒店大堂見到她時不禁眼前一亮,她穿了一套湖水藍色的和服,頭上挽了一個髪髺,人顯得更加清麗脫俗。我說她非常好看,她只是腼腆地說聲「多謝」。她說她父親安排了一架公司車和一個司機給我們用,叫我不用客氣。
我們到達博物館門口時已看見一條長長的人龍,每個人都是靜靜地等待博物館開門,與幾年前我參觀兵馬俑時聽到的喧嘩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
到我們入場參觀時原來也要排隊,跟著一條長龍後面,在每件展品之前不能逗留超過半分鐘。雖然如走馬看花般怱怱一瞥,我還是非常感動:為宋代窰工的非凡造詣感動、為日本人如此珍惜我國的瓷器感動。

南宋吉州窰黑釉木葉紋碗
離開博物館時她說要帶我到小青山參觀一間私人博物館所藏的商、周青銅器和吃午飯,我當然不反對。那間博物館所藏的商、周青銅器並不多,遊人更加稀少,讓我可以細心品味碩大無朋的青銅器。她說她也很喜歡中國古代青銅器,但更喜歡中國書畫。
她送我回酒店時說要讓我補睡一覺,晚上接我一起吃西餐。
晚上七時多我們又在酒店大堂見面,她已換了一身西服,看上去像雍容華貴的少婦,卻好像與她的年齡不相襯,但卻非一般的漂亮。她說她父親晚上要用車,我們唯有徒步走去餐館。銀座的霓虹燈五光十色,路上人如潮水,誠然是一個繁盛的購物中心。
吃完晚餐,正在喝咖啡時她突然有此一問:
“Are you married?”
我衝口而出答道:“Yes, I am”.
她望著我,久久不能言語。我問道:
“What’s wrong?”
“Nothing”,她回答。
在送她回她的寓所的的士上,她捉著我的手問我可不可以多留幾天,說有很多博物館想帶我參觀。我掏出護照一看,竟然剛剛不到半年便到期,後天非走不可。她一臉失望,黙不作聲。下車時她說第二天不陪我,有私事要辦,晚上才跟我一起吃飯。
我回到酒店房間後久久不能入睡,整晚輾轉反側,一直弄不清楚我是否錯過了甚麼。
第二天睡到下午才起牀,一個人吃完午飯後走到日本橋探望一些日本行家,跟他們吃下午茶,聊聊天,很快便到黃昏。
她前一天說會帶我去新宿食壽司、喝清酒。見面後,我們走到一間面積不大的小飯店。酒過三巡,她的臉蛋皃開始紅粉緋緋,我看著,看著,不由得儍了。
第二天她一早送我到機場,叫我多些探望她,跟她一塊兒逛博物館。
我一直不敢再去。
幾年後她在東京開了一間畫廊,專營中國書畫。我收到她的「邀請函」時心中百感交集,但最終還是沒有去,只托日本行家送了一個花籃。
寫到這裏,我不期然想起柳永的《雨霖鈴》:
寒蟬淒切。對長亭晚,驟雨初歇。都門帳飲無緒,方留戀處、蘭舟催發。執手相看淚眼,竟無語凝噎。念去去、千里煙波,暮靄沉沉楚天闊。
多情自古傷離別,更那堪、冷落清秋節。今宵酒醒何處?楊柳岸、曉風殘月。此去經年,應是良辰好景虛設。便縱有、千種風情,更與何人說?
《經濟通》所刊的署名及/或不署名文章,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,並不代表《經濟通》立場,《經濟通》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。
【你點睇】港府本年度已錄逾2千億元赤字,有議員指或難符基本法力求收支平衡之規定。你認為當局應如何解決財政問題?► 立即投票